| [1] |
ZENG Yong, ZHANG Rui, and LIM T J.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with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: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[J].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, 2016, 54(5): 36–42. doi: 10.1109/MCOM.2016.7470933
|
| [2] |
Paving the path to 5G: Optimizing commercial LTE networks for drone communication[EB/OL]. https://www.qualcomm.com/news/onq/2016/09/06/paving-path-5g-optimizing-commercial-lte-networks-drone-communication, 2016.
|
| [3] |
ZHANG Guangchi, WU Qingqing, CUI Miao, et al. Securing UAV communications via joint trajectory and power control[J].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, 2019, 18(2): 1376–1389. doi: 10.1109/TWC.2019.2892461
|
| [4] |
WU Qingqing, ZENG Yong, and ZHANG Rui. Joint trajectory and communication design for multi-UAV enabled wireless networks[J].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, 2018, 17(3): 2109–2121. doi: 10.1109/TWC.2017.2789293
|
| [5] |
ZENG Yong, ZHANG Rui, and LIM T J. Throughput maximization for UAV-enabled mobile relaying systems[J].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, 2016, 64(12): 4983–4996. doi: 10.1109/TCOMM.2016.2611512
|
| [6] |
ZENG Yong, LYU Jiangbin, and ZHANG Rui. Cellular-connected UAV: Potential, challenges, and promising technologies[J].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, 2019, 26(1): 120–127. doi: 10.1109/MWC.2018.1800023
|
| [7] |
LYU Jiangbin, ZENG Yong, ZHANG Rui, et al. Placement optimization of UAV-mounted mobile base stations[J]. 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, 2017, 21(3): 604–607. doi: 10.1109/LCOMM.2016.2633248
|
| [8] |
ZHAN Cheng, ZENG Yong, and ZHANG Rui. Energy-efficient data collection in UAV enable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[J].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Letters, 2018, 7(3): 328–331. doi: 10.1109/LWC.2017.2776922
|
| [9] |
ZHANG Guangchi, YAN Haiqiang, ZENG Yong, et al. Trajectory optimization and power allocation for multi-hop UAV relaying communications[J]. IEEE Access, 2018, 6: 48566–48576. doi: 10.1109/ACCESS.2018.2868117
|
| [10] |
ZENG Yong and XU Xiaoli. Path design for cellular-connected UAV with reinforcement learning[EB/OL]. http://arxiv.org/abs/1905.03440, 2019.
|
| [11] |
黄长强, 赵克新, 韩邦杰, 等. 一种近似动态规划的无人机机动决策方法[J]. 电子与信息学报, 2018, 40(10): 2447–2452. doi: 10.11999/JEIT180068HUANG Changqiang, ZHAO Kexin, HAN Bangjie, et al. Maneuvering decision-making method of UAV based on approximate dynamic programming[J]. Journal of Electronics &Information Technology, 2018, 40(10): 2447–2452. doi: 10.11999/JEIT180068
|
| [12] |
BLISS M and MICHELUSI N. Trajectory optimization for rotary-wing UAVs in wireless networks with random requests[EB/OL]. http://arxiv.org/abs/1905.01755, 2019.
|
| [13] |
SUTTON R S and BARTO A G. Reinforcement Learning: An Introduction[M]. 2nd ed. Cambridge: MIT Press, 2018: 1–130.
|
| [14] |
LIU Xiao, LIU Yuanwei, and CHEN Yue. Reinforcement learning in multiple-UAV networks: Deployment and movement design[J].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, 2019, 68(8): 8036–8049. doi: 10.1109/TVT.2019.2922849
|
| [15] |
KHAMIDEHI B and SOUSA E S. Reinforcement learning-based trajectory design for the aerial base stations[EB/OL]. https://arxiv.org/abs/1906.09550, 2019.
|
| [16] |
ZENG Yong and ZHANG Rui. Energy-efficient UAV communication with trajectory optimization[J].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, 2017, 16(6): 3747–3760. doi: 10.1109/TWC.2017.2688328
|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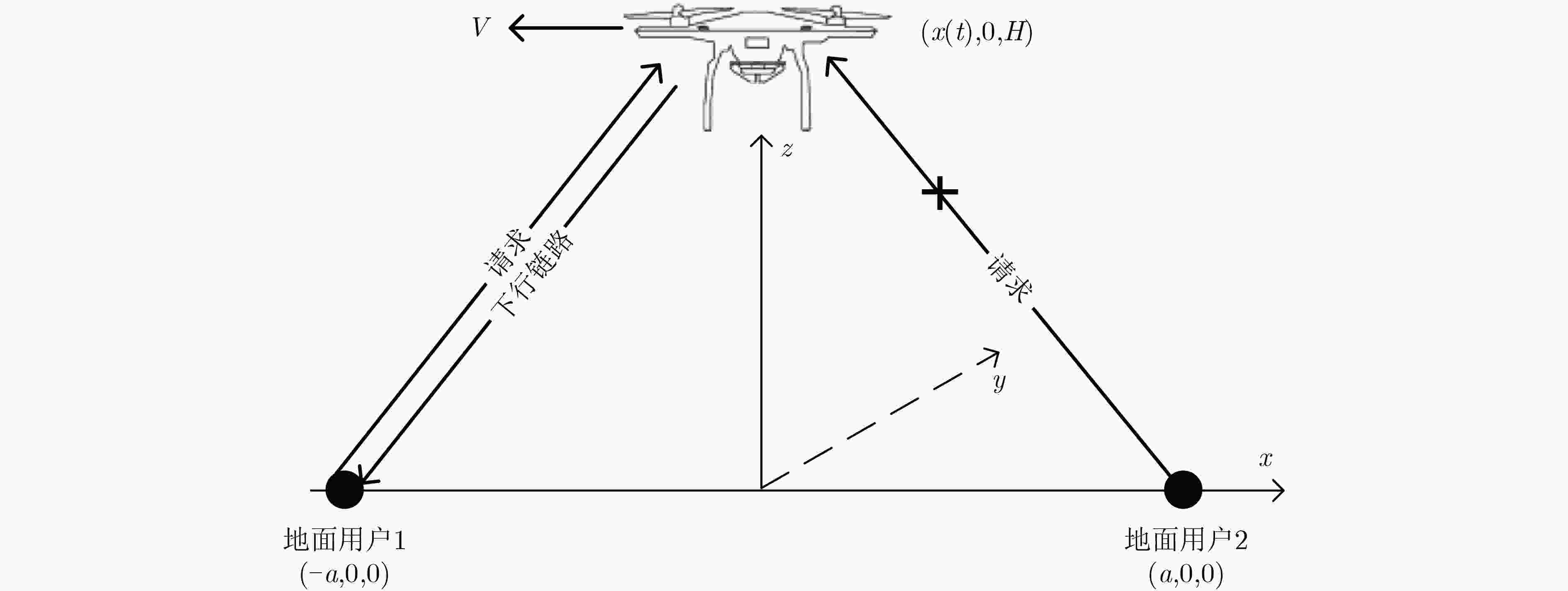
 下载:
下载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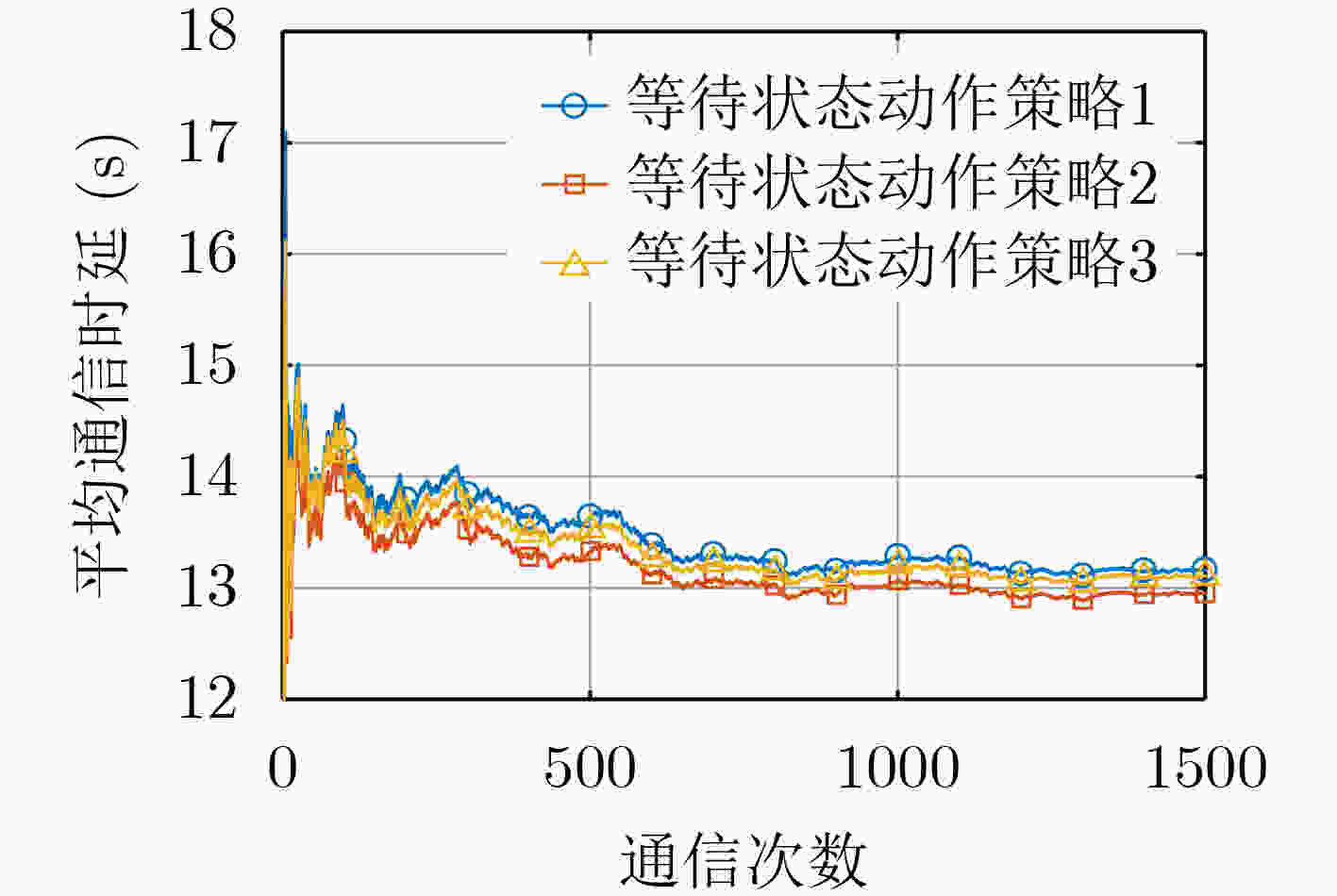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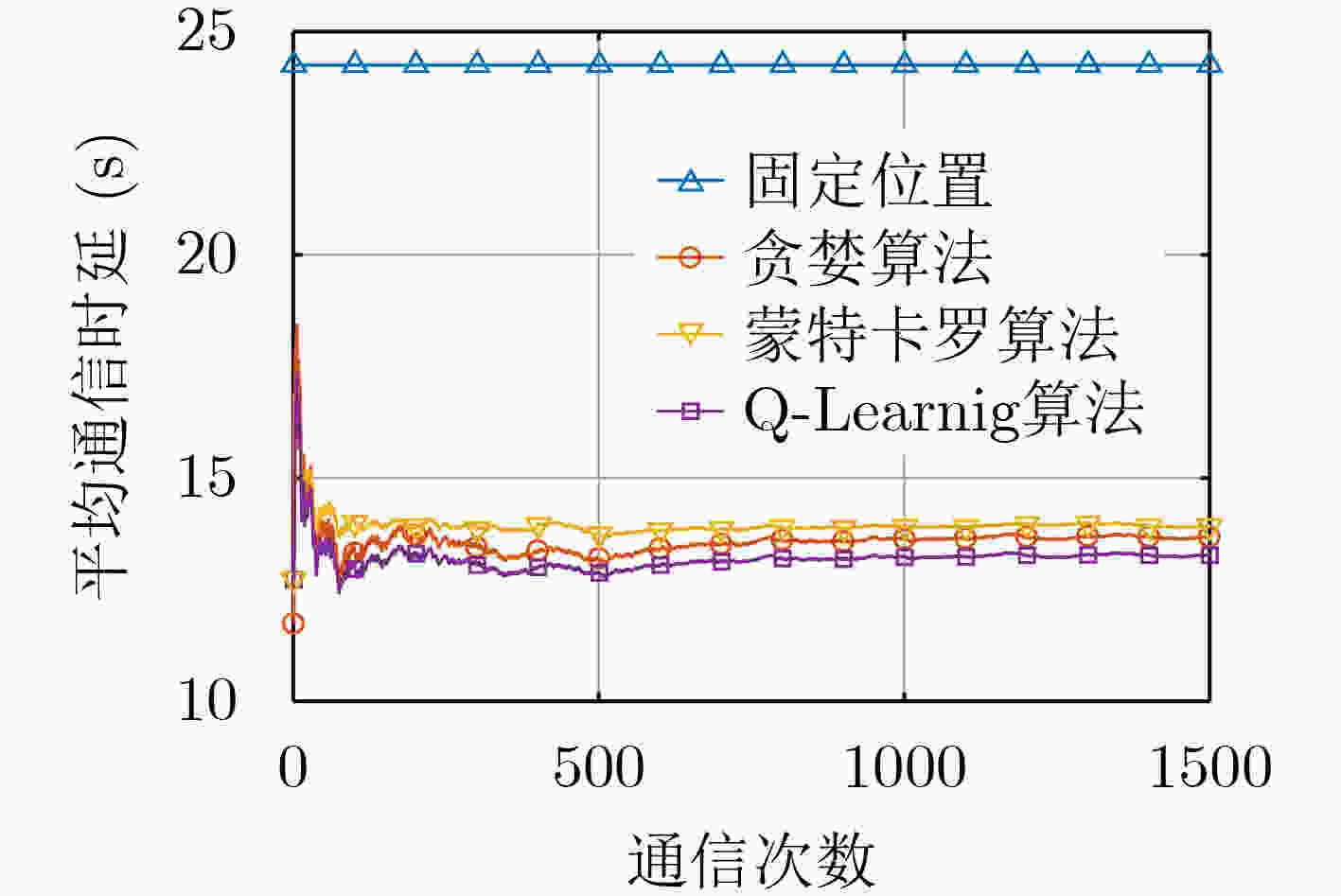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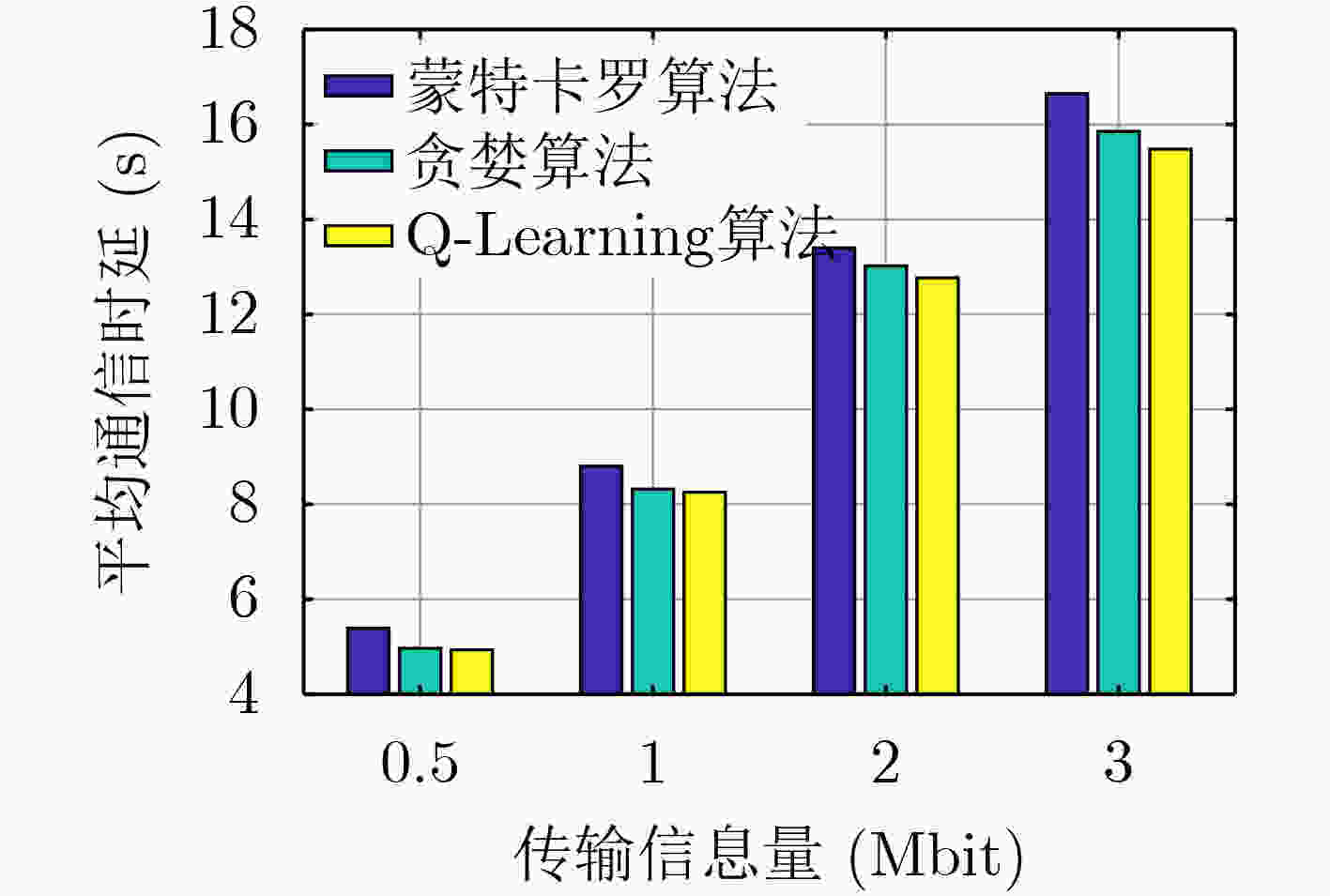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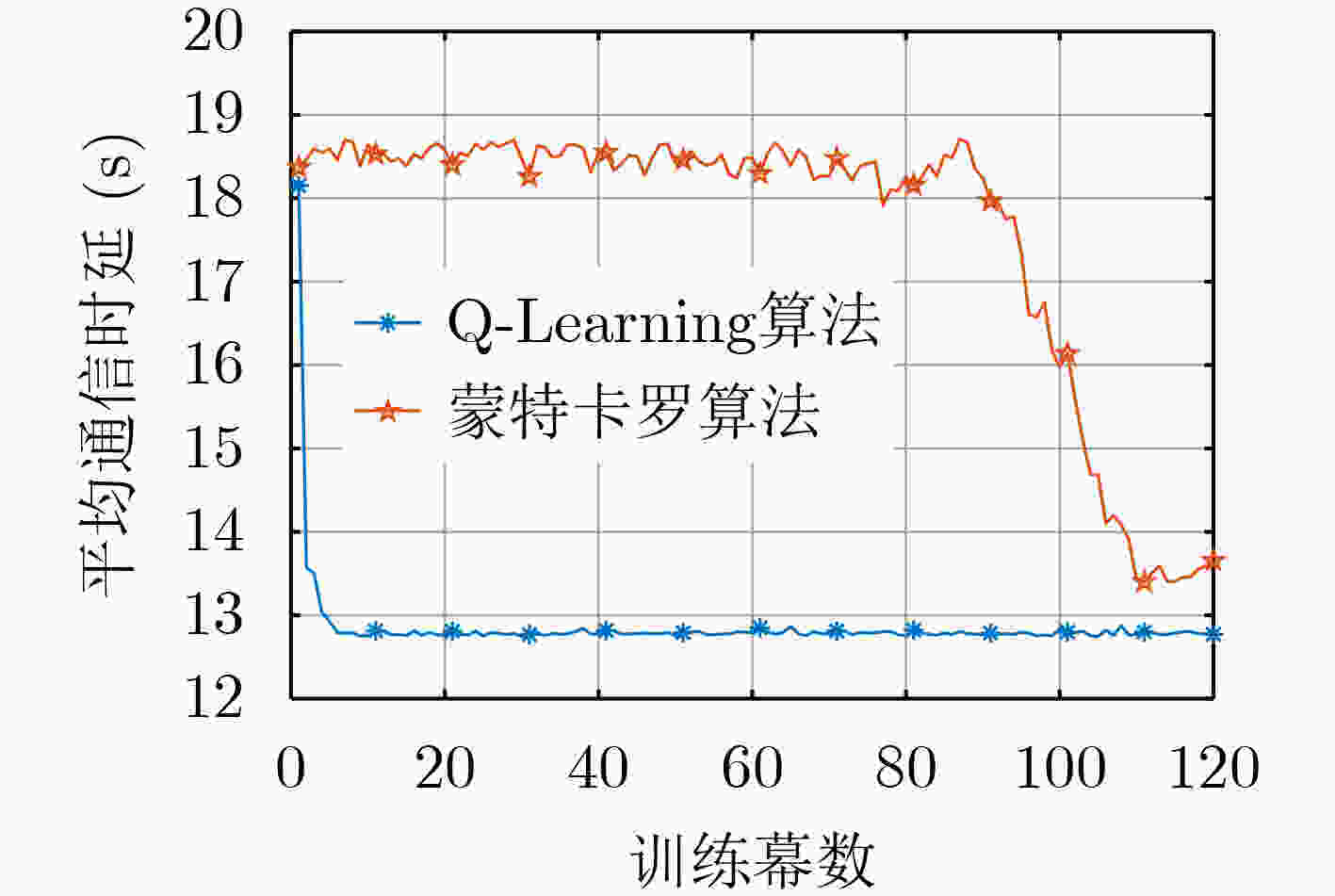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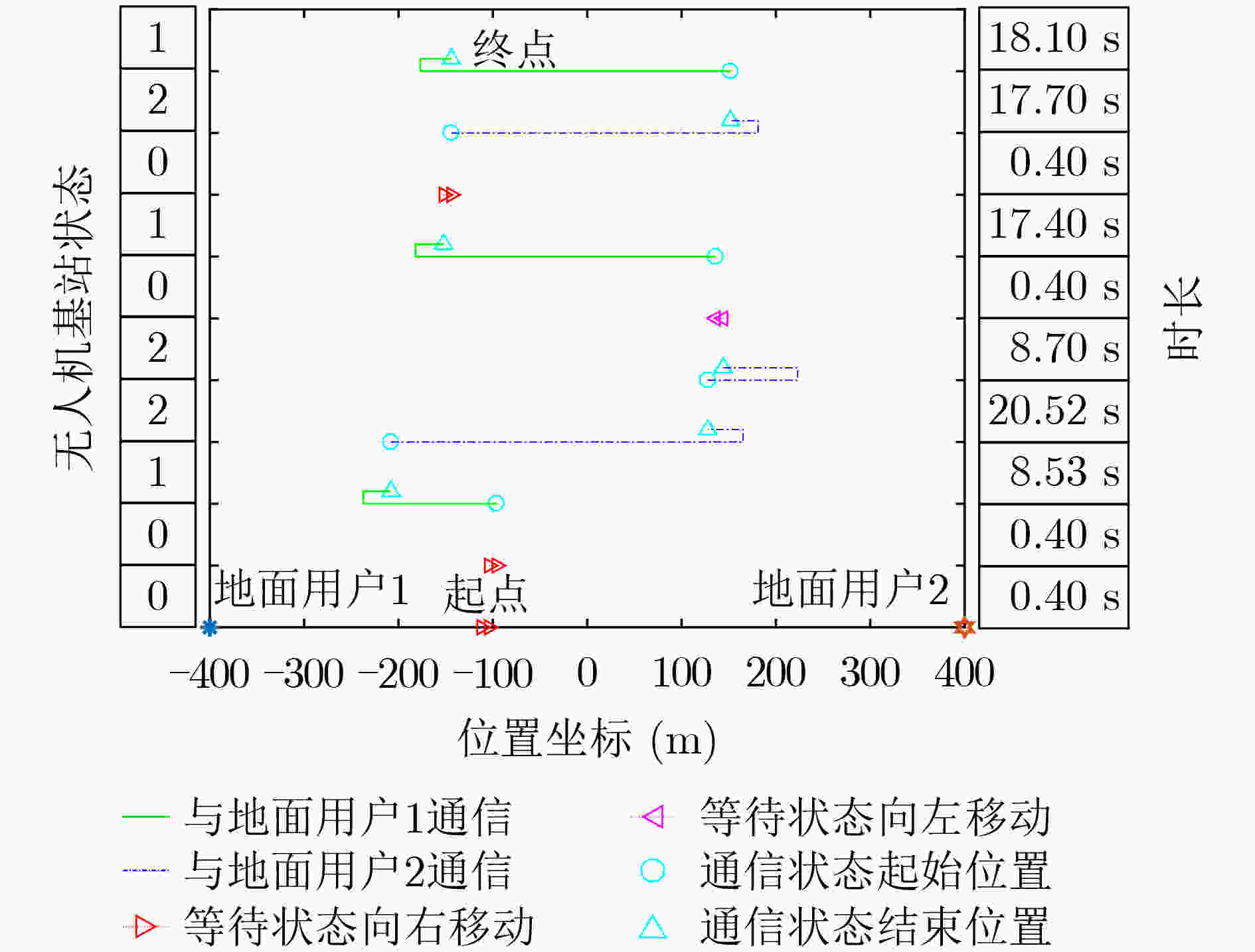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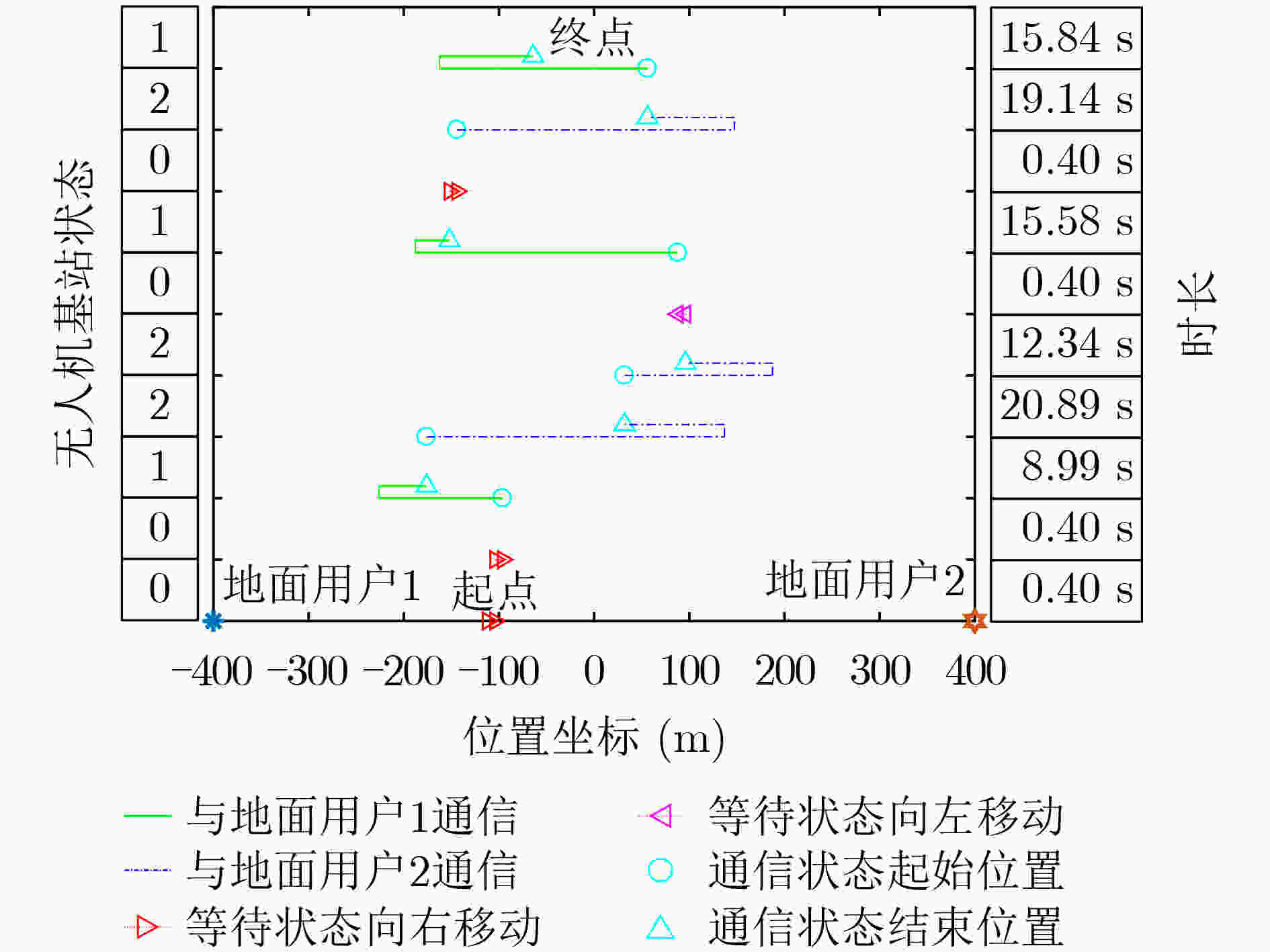


 下载:
下载:
